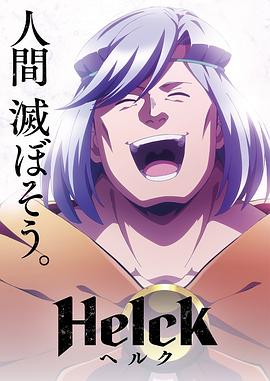相关视频
- 1.釜山行2在线观看正片
- 2.87版红楼梦第8集
- 3.天国的阶梯国语版免费观看全集第6集完结
- 4.我的非常闺蜜(我的非常闺蜜免费播出电视剧)更新至95集
- 5.89我唾弃你的坟墓在线(我唾弃你的坟墓在线观看 rmvb 下载)框架这么掌握,奇妙到爆!HD
- 6.掠夺者电影正片
- 7.郭麒麟新剧《边水往事》正片
- 8.电视剧免费观看电视剧大全在线观全集完结
- 9.新还珠格格在线观看第6集
- 10.我的左手右手全集完结
- 11.今生今世电视剧全集完结
- 12.太阳的后裔 电视剧第5集完结
- 13.最新欧美大片第10期
- 14.恐怖爱情故事之死亡公路 电影第115集
- 15.灯草和尚之白蛇前传第18集完结
- 16.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结局第250622期
- 17.艾米莉在巴黎第07集
- 18.萧十一郎吴奇隆版(萧十一郎吴奇隆版40集歌曲)更新至20250626期
- 19.一夜新娘第一季全集免费观看(一夜新娘第一季全集免费观看西瓜)更新至20250625期
- 20.孝庄秘史电视剧全集免费观看(孝庄秘史电视剧全集免费观看孝庄秘史第七集)HD
《1》内容简介
我没有想过要这么快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,我更没有办法想象,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人,要怎么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,做一对称职的父母。
可是演讲结束之后,她没有立刻回寝室,而是在礼堂附近徘徊了许久。
外面的小圆桌上果然放着一个信封,外面却印着航空公司的字样。
永远?她看着他,极其缓慢地开口道,什么是永远?一个月,两个月?还是一年,两年?
说到这里,她忽然扯了扯嘴角,道:傅先生,你能说说你口中的永远,是多远吗?
听到这句话,顾倾尔神情再度一变,片刻之后,她再度低笑了一声,道:那恐怕要让傅先生失望了。正是因为我试过,我知道结局是什么样子,所以我才知道——不可以。
而他早起放在桌上的那封信,却已经是不见了。
他写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件事,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,可是看到他说自己愚蠢,说自己不堪,看到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,她控制不住地又恍惚了起来。
僵立片刻之后,顾倾尔才又抬起头来,道:好,既然钱我已经收到了,那我今天就搬走。傅先生什么时候需要过户,通知一声就行,我和我姑姑、小叔应该都会很乐意配合的。
……